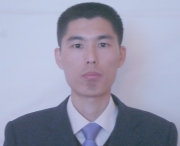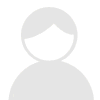《诉讼笔录》 第二部分(9) |
| 分类:生活随笔 时间:(2010-06-10 13:48) 点击:641 |
“我就像《圣经》中的那个人物,您知道,就像那个基哈西,以利沙的仆人: 以利沙让乃缦在约旦河洗七次澡,或做类似的事。为的是治好麻风病。治愈后,他给以利沙带去了一份礼物,可基哈西独吞了。于是,上帝惩罚了他,让他得了乃缦的麻风病。您明白吧?基哈西,就是我。我得了乃缦的麻风病。” “您知道什么?”朱利安娜说道,“噢,您不知道写得最美的诗句有哪些吧?说这话可能显得太自负,肯定的,可我还是乐意告诉您。您愿意我告诉您吗?” 亚当点了点头。她开始吟诵起来: “是,‘甚或我 ——’” 可她的声音突然发不出来了。她咳了咳,继续吟诵: “甚或我无生命而活着, “宛如心中铭刻的形象, “死亡!” 她看了看左侧,看了看亚当左侧几厘米的地方。 “这是维庸的诗句。您知道吧?” 亚当喝了口咖啡。他举手摇了摇。他看了看其他人,他们都在听着,一个个带着几分拘束,也带着几分讥讽。他纳闷为什么让他整天穿着睡衣。也许是为了防止他逃出去?或许尽管衣服上有着一条条纵向的条纹,他穿的不是一件睡衣?这可能是疯人院的服装,或病号服。亚当端起膝盖上的那杯咖啡,喝了个精光。只有杯底还沾着一点液体状的白糖。亚当用勺子刮了刮糖,舔了舔。他真想再喝几杯咖啡,再喝几十杯。他也恨不得把自己的念头说出来。也许对那位年轻的金发姑娘说。他想对她说,留下来跟我呆在这所房子里吧,留下来跟我在一起,我们一起来煮咖啡,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,什么时候煮都可以,然后我们俩一起喝;周围也许有大花园,我们夜里可以去散步,一直漫步到天明,头上不停地有飞机飞过。 戴黑眼镜的家伙摘下了眼镜,看了看亚当。 “如果我听明白了的话,”他说道,“您那位同学的宗教目的,是想造成某种泛神论——神秘主义。通过感知与上帝建立某种联系?是所谓的信念之路,对吧?” 朱利安娜•R补充道: “可这些玩意儿,与您有什么关系?这些神秘主义的事情?那想说明什么问题?您为什么对此这么感兴趣?” 亚当往后一仰。几乎是猛地一仰。 “你们没有明白。你们一点都没有明白。你们知道,对上帝我不感兴趣,西姆也不感兴趣。不存在那样的上帝,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上帝,造物主的上帝吧。它是用来满足某种合目的性的或绝对的需要的,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。他妈的,你们永远明白不了这一点!这提不起我的兴趣。我没有必要被创造,就像这场讨论。它这样并不让我感兴趣,因为它就像一场讨论。可要是它填补了一个空白,就不一样了。一个可怖的、难以承受的空白。介乎于生命层次之间……介乎于两个层次、两个时间之间,你们明白吗?” “可是,那又有什么用,这些神秘主义的玩意儿?”戴眼镜的大学生问道。 “没有什么用。没有什么用。绝对没有什么用。您跟我说话用的词好像都是我不理解的词。您想要这有什么用?我无法回答您。那差不多就像是要我设法跟您解释清楚我为什么不是您——就以鲁伊斯布鲁克为例吧: 对土、气、火、水这不同的物体的本原进行区分,对他来说又有何用?看上去,那可能像是荒唐事。可那并不荒唐。神秘主义使他得以达到一个层次——可不是心理的,不是心理的,嗯?——妙不可言的层次。至于这一层次到底处在什么位置,这无关紧要。也无所谓是哪种层次。重要的,是在他生命中的某个特定时期,他觉得自己对一切全都明白了。正因为与被他一直称为上帝的那一位建立了联系,而就其定义而言,这位上帝是不朽的,万能的,无所不知,无所不在,因此,鲁伊斯布鲁克也成了上帝。至少在发生神秘主义危机的各个阶段如此。也许他不懈努力,在他生命的末期达到了他的层次,达到了自我的彻底袒露。是这样。重要的不是知道,而是知道自己已知。在这个状态,文化、知识、语言和文字都不再有任何用处。简单地说,如果愿意,这也许是一种快慰。可是,决不是自身的目的所在,您明白了,不是其目的所在。到了这一层次,的确如此,就没有多少真正的神秘主义者了。要明白——为了以辩证的方法加以说明——当然,关系是不一样的——人们可以以自身的存在而存在。很简单,这是一个状态。可说到底,这是知觉最终有可能达到的唯一的境界。不管采取何种方式,知觉的最终所在是条死胡同。到那时,它便不成其为知觉。它便成了过去。而在这个阶段,它突然被夸大,变得巨大无比,压倒一切,以至除它之外,任何东西都无关紧要。人们以自身的存在而存在——对,是这样。以存在而存在……”
该文章已同步到:
|
律师统计
加载中...
网站公告
免费法律咨询就上法帮网
文章分类
网站文章
我的好友
友情链接
网友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