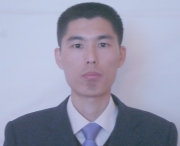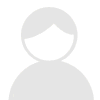《诉讼笔录》 第一部分(12) |
| 分类:生活随笔 时间:(2010-06-10 13:43) 点击:958 |
“懂,懂,我懂。”那人回答。 “那——您,您就没有什么可以讲一讲?” “我?” “对,您,为什么不讲讲?您住在乡下?” 那人往后一退,人群仿佛也跟着退去。 “不,我——” “您在卖什么东西吗?”一个女的问道。 “对,在卖话,”亚当答道。 方才的那位听众仿佛恍然大悟: “您是耶和华证人团的一员吧?嗯?” “不。” 亚当答道。 “噢,那您——您是个预言家,是个预言家?” 可是,亚当没有听清;面对众人的发问,他重又回到他刚开始说的那番话所创造的神秘的黑暗境地,回到他那狂热的孤立境地,回到那赖以栖身的碉堡之中,接着,继续往下讲: “突然,世上的一切全都变了。对,猛一下子,我全都明白了。我明白了这个地球是属于我的,而不属于任何活着的种类。不属于狗,不属于老鼠,不属于寄生虫,不属于任何别的种类。不属于蜗牛,不属于蟑螂,也不属于野草、鱼类。它属于人。既然我是个人,它也就属于我。你们知道是什么使我明白了这一切?是因为发生了一件非凡的事情。是因为出现了: 一个老太婆。对,一个老太婆。一个老太婆。你们马上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我当时在一条路上走,那是一条山路,坡很陡。我坐在这条山路的台阶上,只见山路往下转了一道弯,便消失了。面前,只有一段路,不超过百来米;路面铺着沥青,虽然太阳藏在云层后,可它的光线仍照得路面闪闪发光。突然,我听见一个沉闷的声音朝我传来,我往路下方一看,只见慢慢地出现了一个老太婆的身影,简直慢得可怕,那个老太婆胖胖的,模样丑陋,身着一件肥大的花布宽袖外套,外套像一面旗似的围着她飘荡。我首先看到了脑袋,然后是上身,髋,双腿,最后,是整个人。她正艰难地往山上爬来,什么也不想,大喘着气,像只奶牛似的,两条粗大的患湿疹的腿在沥青路面上拖拉着。我亲眼见她突然从山下冒了出来,好似从浴缸里突然出现,上山朝我走来。她那微弱的身影像个黑点,显现在布满云彩的天际。她是,是这样——她是天地间唯一的一个活动点。周围,大自然全都是一个模样,静止不动——除了,怎么说呢,除了在她脑袋的四周形成的一个光晕,仿佛蓝天和大地是她的头发。城市向大海延伸,小河向大海流淌,高山浑圆如故,青烟始终直线上升。但是一切都是以她的脑袋为起点。仿佛这一切全都失去了平衡。全都变了模样。是她,你们明白吧,原因在于她。是她创造了这一切。青烟,对,完全是人的一个玩意儿。城市,河流,全都如此。海湾也是。高山,山上不见树木,到处都是电线杆子,还有一条条小路和渠道。大道,小路,墙壁,房屋,桥梁,堤坝,飞机,如此等等,都不是蚂蚁!而是她。是她。一个微不足道的老太婆。又丑又胖。甚至都无法生存下去。人体组织全报废了。尽是蜂窝组织炎。走不直。腿上扎着绷带,静脉曲张,身上某个部位长着癌,肛门癌,或别的什么。是她。地球圆圆的,很小很小。人们拿它到处做交易。地球上没有一块地方,你们听清楚,嗯,地球上没有一块地方没有路,没有房屋,没有飞机,没有电线杆。要是想想自己竟属于这种人类,岂不会气疯了?是她。就是她,一包破烂,尽是内脏,尽是脏乎乎、血糊糊的东西,就是这种蠢物,长着厚厚的眼睛,干鳄鱼的皮肤,鲸鱼的须,硬邦邦的子宫,被掏得空空的腺,肺,肿肿的甲状腺,黄黄的舌头,准备结结巴巴说几句……发出像被杀的奶牛似的号叫……那沉闷的叫声……哞哞……哞哞……鼓得像球似的肚子……布满皱纹的皮肤……还有那个脑袋……光光的……胳肢窝尽是毛,七十五年来一直汗津津的,都沤出了口子。就是她。她……你们——你们明白了?” 亚当愈说愈快,快得到了不分句子,不再设法让人听懂的程度。此时,他已经被逼得紧靠在油漆的铁栏杆上;全身只见一个脑袋,露在人群之上,以某种预言家的姿态,以某种友好的形式,面对大庭广众。他成了众矢之的,人们对他指指戳戳,要去喊警察,去找照相机,对他任意嘲笑或侮辱。 “要跟你们说。等等。能跟你们讲个故事。你们知道。就像在广播里。亲爱的听众。我可以讨论。我可以跟你们讨论。谁愿意?谁愿意跟我说话?嗯?咱们可以就某件事讨论讨论?可以谈谈战争。就会爆发一场战争——不会……那就谈谈生活费。土豆价格多少?嗯?据说今年土豆个头很大。而萝卜个头很小。或者谈谈抽象画。要是谁都没有什么可说的。你们没有什么可说的?那我可以讲个故事。是这样的。我可以编造寓言。当场编。听着。我这就告诉你们一些题目。听着。矮棕榈梦想周游东欧的传说。或者。一只被推销员变成姑娘的白 。或者。两只嘴巴的怪人阿斯德鲁巴尔。还有。狂欢节之王与一只苍蝇的爱情故事。或者。佩洛波纳兹国王后泽奥寻找宝物花边排箫记。或者。狂人的勇气。或者。如何捕杀响尾蛇。这很简单。只需要了解三点。响尾蛇。很傲气。不喜欢爵士乐。一看见火绒草,就犯蜡屈症。那么。应该这样下手。您拿起一支单簧管。您见到蛇时,给它扮鬼脸。既然它们很傲气,它们便会发怒,朝您冲来。这时。您就冲着它们演奏《蓝月亮》或《只是个舞男》。用单簧管吹。它们不喜欢爵士乐。这样,它们便会停下来。犹豫不决。就在这时,您掏出来。您从口袋里掏出一朵真正的雪地里生长的火绒草。它们马上就会犯蜡屈症。这时,只需伸手去抓,并对着它们身上的某个部位轻轻地哈气。待它们醒过来。它们发现自己已经不复存在。不再是什么响尾蛇。由于它们傲得可怕,准会受不了。它们宁愿自杀。于是,便屏住呼吸。一憋就是几个小时。直到它们自己憋死为止。它们成了黑乎乎的一团。你们听到了?等等。” 事实真相难以描述,一切都以令人恐怖的速度在发展。事情就发生在一瞬间。人群中出现了骚动,也许还有怒骂。然后,一切又趋于正常。除了这一出人意料的异常情况之外,并没有任何偶然的因素。我想说的是,一切都是那么简单,那么自然而然,以至这样一阵骚动,人们至少为自己赢得了两个小时的时间。
该文章已同步到:
|
律师统计
加载中...
网站公告
免费法律咨询就上法帮网
文章分类
网站文章
我的好友
友情链接
网友留言